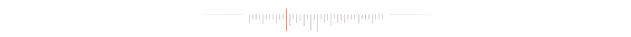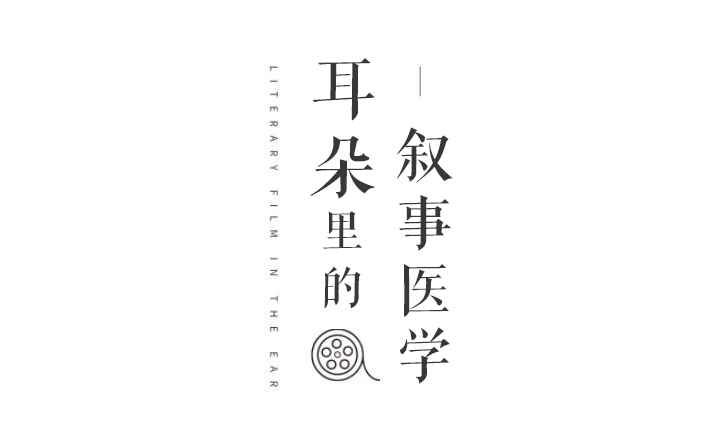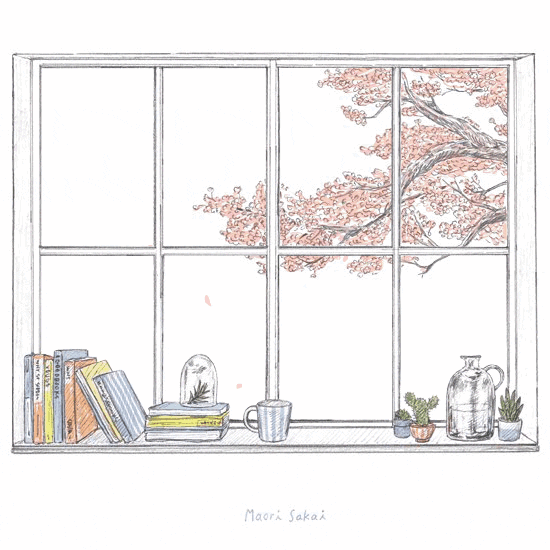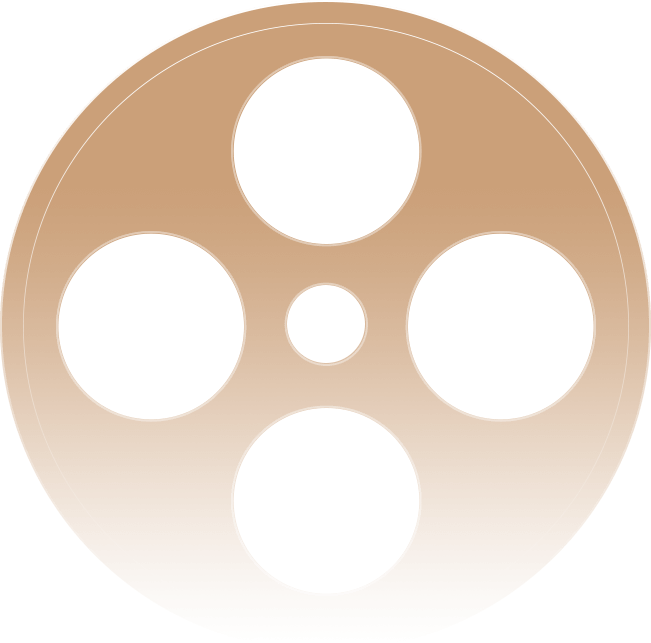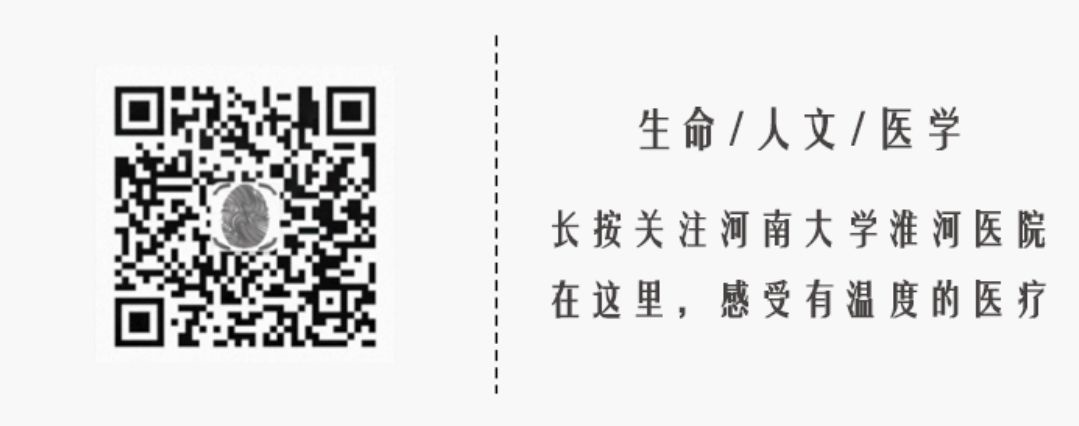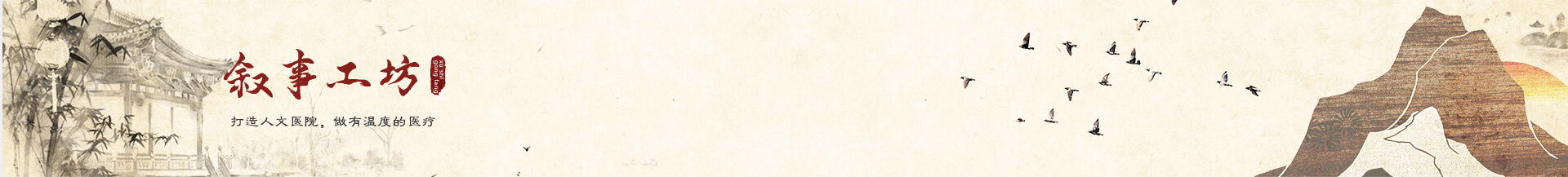第二点,我们可能从故事中悟到了创设故事空间的重要性,故事能够帮助患者重构人生意义,战胜疾病。在这个小故事中,奥斯勒医生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他能够换视角的理解妻子的伤痛,又能创造性地使用夭折的孩子的叙事语言,创设了孩子在另一个空间里愉快存在的生活点滴。虽然奥斯勒为妻子创设的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个故事比现实生活中丧子的悲痛故事更能让妻子接受,更能抚慰她的内心,因而,在两者之间,奥斯勒的妻子选择进入了同时作为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奥斯勒为她创设的故事当中,使她的心身都得以解脱。作为人文主义医生,奥斯勒为患者创设故事的例子不胜枚举,找机会再与大家分享。
听到这里啊,大家可能要问奥斯勒先生的叙事素养是从哪里来的呢?奥斯勒曾经说过:“没有书本做导读来学习患者的临床症状,就好像没有航海图来到海上航行。只读书本,就好像学习航海,却从来没有出海航行过。” 奥斯勒告诫医生每天都要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还为医生列出了枕边书清单。奥斯勒提倡我们“要用生命的诗句来鼓舞我们每天例行的诊疗工作”,奥斯勒阅读了大量有关生老病死的叙事性书籍 ,藉此拥有了极高的叙事素养,这也是叙事医学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原因。
第三点,大家可能会想到,医护患三方的叙事素养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在这个故事里,奥斯勒既是患者,又是患者家属,因为作为孩子父亲,他一定也因丧子而心身俱伤,但他同时也是医生,能够在三个身份中自由转换,因而,他更好的利用了换视角思考的契机,理解不同主体的内心和情感。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个故事移置到普通的医患之间。丧子的A患者因身体各种不适入院,C医生成为她的主管医生。根据A患者的体检报告,C医生起初也用了各种药物,如改善肠胃功能,提升食欲的药物,治疗失眠、改善睡眠的药物,治疗心脏、改善心悸的药物等等,但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A患者仍魂不守舍,身体不适,日渐消瘦。
这时,C医生开始思考药物不起作用的原因,转向直接与A患者进行交流,很耐心地聆听了她丧子的故事。之后,C医生以A患者孩子的名义,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日常点滴,A患者看了信之后对死亡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了慰藉,最后,在没有继续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身体康复出院了。A患者没有因为起初C医生开的各种无效药物而去投诉他,还对C医生心怀感激,全程没有出现任何医疗纠纷,一年之后A患者的第二个孩子健康降生,他还与C医生分享了这个喜讯,并对医生当时能够用心帮助表示感谢,这是不是皆大欢喜呢。
事实上,当医生用温暖而友善的目光、同情的充满智慧的叙事性语言和理解包容的态度耐心地聆听病患者讲述自己患病的故事时,和谐的医患关系就建立了起来。因为疾病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患者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诉说,有情感要宣泄,有心理压力要释放。临床实践表明,医患良好的叙事沟通本身就是在治疗。因为对于慢性病和重症患者而言,患病意味着日常生活结构出现断裂,在突遇的暴风雨当中突然失去了一直在指引人生之路的生命地图。这时的患者故事也遭遇了“叙事触礁”,不知道自己的故事将去向何方。医护人员的叙事素养能够帮助他们弥合这个断裂,在重新认识生命故事和生命意义之后,战胜暴风雨带来的各种灾难。
从以上三点启示来看,叙事素养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参与临床实践前就应该培养的一种人文修养。叙事医学把叙事素养或者叙事能力概括为“认识、吸收、解释”疾病的能力,它注重的是医护人员“由内而外”的软实力。通俗一点来讲,叙事医学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和病患本人及病患家属遵循叙事规律共同参与临床过程的一门交叉性学科。叙事医学总是强调“治病”过程是“医护患”以及患者家属多方共同参与的过程,而非单纯的医护单方参与。